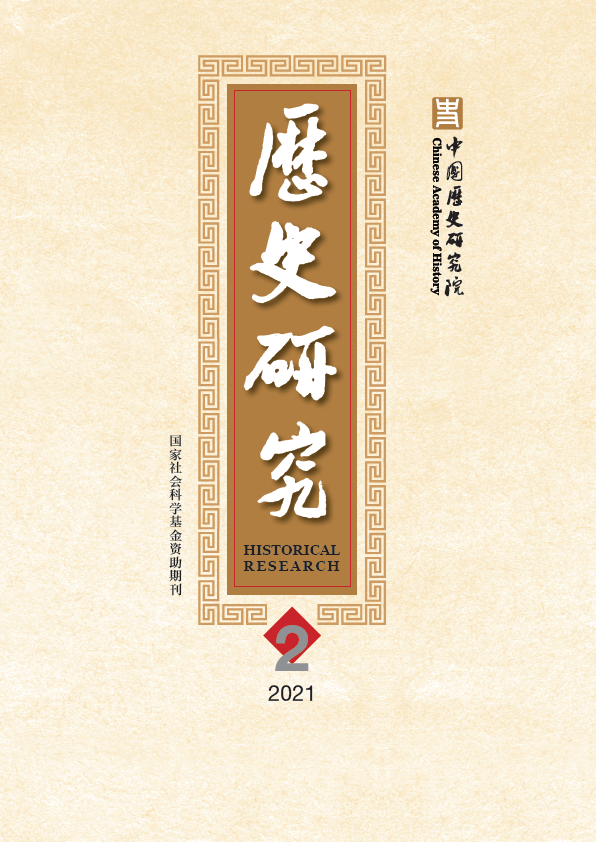
摘要:南宋理学家吸收了源自纬书的拟人地理观念、唐代一行的山河两戒说,以堪舆视角重整《禹贡》山川,创造出一套中心化的地理秩序。经过元明两代理学家与堪舆家的接引与改造,逐渐演变为以论证皇权为目的的三大干龙说,并为社会各阶层所公认,此即沉淀为明清时代一般知识与信仰的中国龙脉论。龙脉论是真实山川与想象地理的重叠,它既是流传于一般社会中的宏观地理观念,也是文人精英与堪舆术士共同发明的皇权正当性学说。它的形成,是流行于不同阶层的多种知识传统在王朝政治格局中杂糅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禹贡》 朱熹 堪舆 龙脉
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山河形势往往在自然、军事或行政区划地理之外,被赋予信仰或政治的意义。进入国家祀典的五岳四渎、道教的洞天福地,都属于这种地理知识的再阐释与再加工。流行于明清时期的三大干龙说,认为天下山川可以分成源出昆仑山的三条主干,中国所有山脉皆从三干分出,这套理论既是堪舆术所依凭的世界观,也是一般社会理解宏观地理的基本框架,世俗所谓“中国的龙脉”,主要也是指这套理论。以往学者对三大干龙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过或重在讨论晚明地理学家王士性的贡献,甚至直接归在王氏名下;或将其视作堪舆家的发明,把它当成神话或堪舆地理学来讨论。其实,三大干龙说的来源非常复杂,它脱胎于宋元禹贡学所代表的地理知识,也渊源于朱熹所整理的政治化、中心化的天下山川系统,又被元明堪舆术士赋予论证皇权的功能。本文追溯三大干龙理论的来龙去脉,尝试展示它在不同时代的复杂面貌,探索地理、信仰与政治的多层次关系。
一、对天下山川大势的早期理解
中国古人对宏观山川形势的理解,有悠久的知识传统。中国现存最早的两部地理学文献——《山海经》和《禹贡》,都讲到了天下山川的条理。《山海经》的《五藏山经》部分记述五个方位的群山,各分若干条列,不论这些名目与真实的地理是何种关系,这种叙述方式都反映出当时对山体宏观脉络及走向已经有所认知。一些经学家认为,《禹贡》叙述大禹导山,实际上也在把山脉分成条列。马融、王肃把大禹疏导的各座大山从北至南分成三条,郑玄又把三条中的南条分成二列,这样就成为四列。三条四列最北为碣石,最南为衡山,大体相当于汉代知识阶层所熟悉的华夏范围。经由历代经学家解释,《禹贡》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被看作华夏文明永恒的核心区域。但是,无论是《山海经》还是《禹贡》,它们所描述的原本只是天下山川的自然分布,强调的是天下的整体性,而非等级、秩序或界限。
与此相异的是《史记·天官书》中所记录的天下山川之“维”。《天官书》说“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这里所说的“秦并吞三晋、燕、代”,指的是战国末年的局势。这条起于陇蜀、没于勃碣的山川之维其实就是华夷分界,是利用星象对内夏外夷格局所作的地理学解释与确认。自然,《禹贡》那种混一式的天下观仍然存在,与《天官书》中可以上应天象的华夷分立的地理观念并行不悖,并在后世随着夷夏格局的变化而此消彼长。
山川界限体现华夷之分的观念影响后世至为深远,唐代一行的山河两戒说也是这种观念的苗裔。根据《新唐书·天文志》,一行曾提出南北两戒说:“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在两戒之内的华夏区域,一行又根据水系将其分为两河,北河包括黄河、泾水、渭水、济水等水系,南河包括长江、汉水、淮水等水系。
两戒、两河是一种复合的天下地理二分法:两戒分开华与夷,两河又将华夏地区一分为二。这套系统是一行的主观创造,与他的天文分野观念密切相关。但是,根植于古老传统的地理脉络观念,往往与现实的政治变迁出现扞格。假如严格按照山河两戒的说法,则唐都长安及李唐王室起家的太原都在北戒之外,北宋税安礼所绘《唐一行山河两戒图》正是这样画的,整幅图因此呈现以宋代两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为主轴的政治景观。似乎是觉察了这种不妥,南宋唐仲友所绘《唐一行山河分野图》就有意将经过关中地区的北戒向北略移,这样京兆(长安)才得以在两戒之内。宋人的游移,固然有对政治地理的敏感因素在内,但也说明在地理学的视野中,一行的理论由于受到分野传统与自然山川的双重限制,并不能充分解释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
与《史记·天官书》和山河两戒说将山脉视作文化及政治界限不同,源自《河图》《洛书》一系纬书的地理观念,则在宇宙论意义上将大地描述为一个互相连通的有机整体,同时强调作为大地中心的昆仑山的重要性。河洛纬书地理学的要义有二:其一,昆仑山为大地中心,黄河所出,上有铜柱通天,赤县神州在昆仑之东南,居天下九分之一,其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其二,大地之中有孔道互相连通,“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和气所出”。在此基础上,河洛纬书以大河为线索,建构起一套拟人化的大地观念,而作为这个拟人化大地各个器官的,多数是《禹贡》名山。
河洛纬书以昆仑山为中心的宏观地理观念已经超出了经验世界,类似的理论至少起自战国时代,很可能与邹衍一流的方士有关。这套观念虽然不像五岳那样进入祀典,成为国家正式承认的神山系统,却一直流传有序,化作一般地理知识。《楚辞·天问》、《淮南子·地形训》、传为尹喜所作《关令内传》、西晋张华《博物志》、唐代类书《初学记》、宋代类书《事类赋注》等,都将“九州八柱”作为基本的地理架构。大地下有空洞、“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的观念则进入道教,参与了洞天福地系统的形成。不过,河洛纬书的拟人地理重在西北,道教的洞天福地却多在东南,这是南北朝以后文化重心转移的一个表征。
《禹贡》的山川条列、《史记·天官书》及山河两戒的华夷之分、河洛纬书的拟人地理,都成为后世龙脉理论的知识资源。不过,上述种种理论都只针对自然地理,并不涉及都邑、人居,后者主要是相地术关注的领域。
在后世堪舆家看来,相地术本来就起源于上古圣王的都邑选择,《汉书·艺文志》所说“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形法家,常被追认为堪舆术的滥觞,以示择地并非小道。但是,都邑选择的实践机会非常少,实际的决策过程又相当复杂,不太可能预先设计出一套术数理论,临事行用,所以自《汉书·艺文志》以后,都邑选择术在相地类文献中几乎消失。直至唐代,敦煌写本相地术典籍才再度出现“大举九州之势”的论述,但其落足点却在阳宅主人的个人荣利,而非城址的选择。北宋的择地术官书《地理新书》有“城邑地形”一篇,不过从该篇所引诸家之说看,所论并不是城市选址的原则或技术,而是既有城邑政治地位或人文地理的术数论证,包括民风、科举、人民生计等方面,其具体依据则是以术数整理排布的城市山水环境,并不涉及对天下山川总势的理解。
较早将相地术建构在宏观地理观念之上的,是传说为唐末杨筠松所作、实际可能成于南宋的《撼龙经》和《疑龙经》。《撼龙经》将佛教四大部洲的世界观缩小改造为一个中国式的天下版本:须弥山位于天下中央,从中生出四条龙脉,西、北方向高山峻岭不可知,东方之龙进入朝鲜半岛,只有南方之龙进入中国,分肢擘脉,与长江、黄河等水系气血勾连,形成大小不等的都邑、郡县、市镇。这个天下是以山脉为骨干生长而成的,人类聚居之所亦依凭山脉而形成。《疑龙经》则强调龙分枝干,寻龙首先应判断是枝龙或干龙,龙脉的层次决定了垣局的等级,“长作军州短作县,枝上节节是乡村……凡有枝龙长百里,百里周围作一县”,而天下的格局,也就由这长长短短的干龙、枝龙所决定,“若以山川分两界,黄河川江两源派。其中有枝济与河,淮汉湘水亦长源。干中有枝枝有干,长者入海短入垣”。显然,这也是一种类似山河两戒的南北两分法。
三条四列所描述的山川系统是并立式的,并不在山脉或地理区域中分出等级;山河两戒重在华夷之分,不涉及两戒之内华夏地区的山川;五岳虽以泰山为尊,但主要仍是均匀分布式的神山系统,而且五岳地位虽高,却不与其他山脉或名山构成等级上的联系;纬书中的神话地理描述了以昆仑山为中心的大地,所有的山脉都可以被纳入这个系统,不过这种中心向外生长的山脉结构类似一种宇宙模型,无关人间秩序。但是,《撼龙经》《疑龙经》所述天下山川大势却是等级化、秩序化的。
《撼龙经》《疑龙经》出自江西。朱熹曾说当时“地理之学出于江西、福建者为尤盛”。根据明初的说法,江西堪舆之学重视山形水势,称作“形势派”或“峦头派”,杨筠松被追溯为这一流派的源头,以龙脉理论来观察天下山川也被认为是形势派堪舆术的特征之一。至晚在明初,形势派已经成为南方堪舆术的主流,“其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为什么形势派堪舆术(至少在儒家士人的描述中)赢得了竞争的胜利?其实,南宋至元代的理学也是“出于江西、福建者为尤盛”,形势派堪舆的流行与理学的介入有着密切关系。
二、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
在宋代以后的堪舆传统中,朱熹被赋予宗师地位,许多风水书都会征引他的言论,作为论证风水术合理性的有力证据。朱熹本人不仅对风水技术有相当兴趣,而且以一个理学家的视角重构了风水术的理论基础,将程颐所称“最无义理”的风水术“义理化”,这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不过,除了淡化风水术吉凶祸福的色彩并将其纳入理学的理论系统之外,朱熹对于风水术的重要影响还在于,他以风水观念解释宏观的山川形势,成为堪舆地理学的奠基者。
朱熹认为,天下最形胜之处在河东(北宋河中府,今山西南部运城一带)。《朱子语类》记:“尧都中原,风水极佳。左河东,太行诸山相绕,海岛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绕,直至泰山凑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庐山诸山。第三重自五岭至明越。又黑水之类,自北缠绕至南海。”朱熹还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在朱熹的描述中,北至云中,南至五岭、南海,宋人理解的整个“中国”都是为了拱卫“风水最好”的河东,而河东的“好风水”总是与其为尧舜禹故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河东地形极好,乃尧舜禹故都”;“河东河北皆绕太行山。尧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河东之地的风水地位与尧舜禹的历史彼此呼应。
为了描绘出这个中心,朱熹重新定义了山川的走向。一行的北戒,系从三危、积石出发,经过终南山东至华山,越过黄河成为太行山,再向北成为燕山。在这个脉络中,太行山的走向系自南而北。朱熹则说,太行山是从云中发脉而来,“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太行山自西北发脉来为天下之脊”。太行山成为河中府的龙脉。风水术中,山的走向就是“气”的走向,朱熹强调“云中正高脊处”,以及太行山东西河流的流向不同,其含义不言而喻,那就是强化“太行天下脊”的角色,以配合河中府的神圣地位。
朱熹反对以“三条四列”理解《禹贡》,认为“《禹贡》本非理会地脉”。他的证据是,《禹贡》言“道岍及岐,至于荆山”,若如注家所说这是描述地脉的话,那么地脉要从岍山、岐山到荆山,再跨越黄河,然后成为壶口、王屋、碣石等山,这样说来太行山将是从荆山而起了,未免太过荒唐。朱熹坚持认为,太行山从西北发脉而来,乃是天下之脊,如果要讨论地脉的话,必须从这个“中国大形势”出发。如果按照形势派风水家习用的术语来说,河东是中国最大的吉地,后有太行山为来龙,左右有泰山、华山分别为青龙砂、白虎砂,前有嵩山为案山,再前有淮南诸山、江南诸山、五岭为重重朝案,黄河为水,自西北而来,在吉地之南缠绕东去,这就是朱熹描绘的天地风水系统。
朱熹身处南宋,他又如何处理北方女真政权在政治地理中的位置?他说:“天下惟三水最大:江河与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所出,虏旧巢正临此江,斜迤东南流入海……河东奥区,尧禹所居,后世德薄不能有。混同江犹自是来裹河东。”天下大水,古来有江、河、淮、济“四渎”的说法,朱熹删去淮、济,然后加入混同江,并且指明“虏人之都,见滨此江”,暗示女真旧都也得到天地山川格局的加持。虽然“混同江”究竟指的是哪条河,历来有不同看法,但朱熹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虏人之都”、“虏旧巢”就是位于今松花江附近的金上京会宁府。他说混同江“斜迤东南流入海”,这是把松花江—黑龙江与鸭绿江弄混了,但即便如此,“混同江犹自是来裹河东”一语在真实世界的地理中也难以理解,可以说是朱熹将女真故地与以河东为中心的华夏风水系统强行“焊接”的明证。“裹”字意味着混同江也是朝向河东,这样河东就不仅是宋代所谓“中国”的中心,也是包括金朝在内的“天下”的中心。
但是,以河东为天下最大吉地,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北宋汴梁、南宋临安,还是汉唐旧都长安、洛阳,都变成了临时首都,只有晋南的一小块区域,理应成为永久不移的华夏政治中心。为何朱熹对当时天下地理图景有如此大胆的改造?
首先,在朱熹的时代,原有的大地秩序观念在多重挑战下面临严重危机,亟须重构。朱熹的理论,一方面出于“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是对华夏正统的地理追认。本来,传统观念认为洛阳为大地之中,四方贡赋道里均,这成为以洛阳为都城的王朝的重要依据,不同的王朝都曾用各种方式来证明。可是,由于佛教世界观的传入及天竺地理知识的流布,特别是随着地理测绘技术的进步,到了宋代,这一观念已经被彻底动摇。在官方的天文地理学中,开封附近的浚仪县岳台被认定为大地之中,但这个新晋地中仅是地理位置的几何中心,不像洛阳那样有经典和传统的支持,严重削弱了华夏王朝地理空间的秩序感,连朱熹也不能解释天下中心为何汉代在洛阳附近的阳城,宋代就移到了岳台,只能猜测是“地气之转移”。此外,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中原中心主义的地理观越来越受到质疑。在后世看来,宋代疆域远不如唐代广阔,但由于儒家文明在宋代的推广,特别是南方的开发,宋人反而觉得当时华夏地域已远非唐代的山河两戒所能限制。南宋陈藻就在几次策论中反复问及,本朝蜀地文教发达,“三苏,文人之翘楚也”,而且“今日则七闽之儒风为盛,且骎骎而逾广矣”,这些都在南戒之外,一行视作蛮夷之地;至于中原,一行说是文教之地,但西晋以后中原云扰三百年之久,靖康之后又沦为兵战之区,又当如何解释?“地脉最难寻者也”,三条、四列、两戒之说各有缺陷,且与《禹贡》相冲突,该如何理解?
宋室南渡后,中原地区及黄河都沦于“夷狄”之手。陈藻的发问暗示,缓慢的文化变迁加上激烈的政治变动,原有《禹贡》或山河两戒式的地理秩序都变得岌岌可危了。在这样的理论空白中,朱熹抛弃将天下几何中心神圣化的传统做法,借助风水原理,创造了中国地理空间的新秩序,重申了中原地区的重要性。他身处偏安的南宋,谈及天下山河大势时,仍抱持以中原为中心的大一统视野,完全无视宋、金、西夏各自建立政权的政治现实,这自然是“恢复”的地理宣示,更显见一种包容整个华夏地理区域的政治地理学在此时已经定型,不再受王朝疆域变化的影响。这不但是对《禹贡》九州作为华夏故土的再确认,而且纳入了女真故地,更强调了天下地理的秩序感。
其次,朱熹之所以用风水视角来重整山河秩序,不仅是因为他对风水技术相当熟悉,还因为南宋理学家的地理观念本来就与风水术有密切关系。朱熹未必及见《撼龙经》《疑龙经》的成书,不过他是郭璞《葬书》以下比较重视山川形势一派的支持者。今本《葬书》成书于两宋之际,龙、砂、水、穴、朝向、拱卫这些描述山川形势的堪舆概念最晚在当时已经正式形成。该书《形势篇》概述山川形势与吉地之关系,是形势派堪舆术的经典文献,其中说“龙虎抱卫,主客相迎”,陈注“谓左右拱护,前后朝揖也”,分明就是朱熹天地风水论的观念与术语来源。他在《山陵议状》中所说“若以术言,则凡择地者,必先论其主势之强弱、风气之聚散、水土之浅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后可以较其地之美恶”,就足为明证。朱熹相信《葬书》,以至于杨万里还写信委婉批评他:“然景纯《葬书》,东汉以前无有也,老先生岂亦微信其奇怪乎?”朱熹对天下风水大局的判断也完全符合术家的要求:风水宝地要有环抱、有朝护,藏风聚气,正所谓“水绕砂回,拜舞类君臣之象”,河东就宛如天下山川之君。
在朱熹前后,一些理学家还尝试将真实的地理作为堪舆术的知识基础,将山川形势从术数化的世界中抽离出来。与朱熹关系密切的前辈蔡发所著堪舆原理《发微论》,先讲天地生成的过程,接着说“凡山皆祖昆仑,分支分脉,愈繁愈细,此一本而万殊也;凡水皆宗大海,异派同流,愈合愈广,此万殊而一本也”,将“理一分殊”的理学核心观念引入地理学和堪舆术,成为理解山川形势的理论基础,这其实是河洛纬书地理学的理学化。不过蔡发除了重复“凡山皆祖昆仑”之外,还提出“凡水皆宗大海”与之对应,又比纬书的地理学精致。《发微论》以龙、砂、水、穴论风水,它所提出的动静、聚散、向背、顺逆等若干哲理性原则,成为后世形势派堪舆术的理论基础。以此书为标志,堪舆术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地理世界观,朱熹的天地风水论也建构在这种理学化的风水世界观之上。
朱熹虽然将河东看得非常重要,但绝不等于他将其当作天下地理的几何中心。在与学生的问答中,朱熹提出其实有两个地理几何中心:倘若以整个天地宇宙来看,则昆仑是中心;倘若以“中国地段”来看,则“豫州为天地之中”。所谓“冀都是正天地中间”,主要是从风水“形势”着眼,而风水中所要求之“吉地”或“穴”,重在后有来龙、前有去水,左右有环抱,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是形势中心,是“气”之蕴积之处,不需要甚至根本就不能处于几何中心(他还说过“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
目前文献所见,朱熹是第一个从风水形势角度重新整理中国山川系统的人,无论是从地理学还是风水术的角度来看,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都有其独创性。但这不妨碍我们进一步追问,朱熹如此尊崇河东,究竟是他的独见,还是有更普遍的思想背景?
传统社会中,精英文人的地理观念奠基于《禹贡》。要了解朱熹时代士大夫对天下地理的理解,首先需要回到当时的禹贡学。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初极为繁荣的《禹贡》注解中,独尊冀州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对冀州的强调,其实就是对尧舜禹之都的强调、对皇权的强调,这是南宋初年禹贡学的时代共识。
《禹贡》九州,首列冀州,其中原因何在,现存的汉晋人注解对此并未深论。唐代孔颖达认为,九州的顺序是按照大禹治水的次序排列的,虽然冀州是帝都所在,但这并非其高居九州之首的原因,“若使冀州之水东入兖州,水无去处,治之无益,虽是帝都不得先也”。这个以《禹贡》为治水指南的思路在北宋仍然延续,北宋禹贡学仍以“水学”为核心。
南渡以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经解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林之奇反对“以治水为先后”的理解,认为《禹贡》只是记“九州之经界与其田赋贡篚之详”,而在这样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其他八州都记载经界,只有冀州没有经界,“别帝都也”。为了证明《禹贡》突出帝都的特点,他比较了《周礼·职方氏》的记载方式,说后者将周代王都所在之豫州混同于诸州之间,“非特不能别王都之所在,乃并与九州所止之方无所辨别也”,结论是《禹贡》“独出于千载之上,非后世地理家之所能及也”。这样,《禹贡》就并非治水之书,而是政治文本了。
这种以冀州起首是为了重帝都,重帝都是为了尊王的论调,在南宋初年的禹贡学中非常普遍。史浩就以激烈的语调说,假如大禹治水不从帝都开始,那就是不知“急务”,不合“爱君之志”,尧既已都冀,“率土之滨,皆知归向……孰不奔走于阙庭之下”,《禹贡》所记根本不是治水的过程,乃“禹教天下以尊君亲上之大义”。吕祖谦认为《禹贡》所述水道,乃“一人统天下之大,丝牵绳联”之漕运通道;袁燮说,“天子为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贡,不容有一州之路不通于王畿”。其他如薛季宣《尚书古文训》、夏僎《尚书详解》、黄度《尚书说》等,都无一例外强调冀州的王都地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蔡沈(蔡发之孙)《书经集传》折中众说,引晁说之“王者无外之意”一语,《禹贡》遂在南宋人的解释中成为尊王之书,尊王的表征之一即冀州凌驾于其他八州之上的超然地位。
南宋初年,赵宋王室摇摇欲坠,维护皇权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之一,北宋初年萌生的尊王潮流再度高涨,以《禹贡》尊王就是这种思潮在经学中的投射。朱熹本人也曾认真讨论大禹治水的顺序,他承认治水确实应该是“先从低处下手”,但认为《禹贡》文本的顺序与大禹治水的顺序没有关系,“窃意当时治水事毕,却总作此一书,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毕,总作一门单耳”,《禹贡》其实是治水结束之后开列的工程清单,因此须以王都为首。治水顺序是技术问题,《禹贡》文本顺序是政治问题,在以《禹贡》尊王这一点上,朱熹与同时代的尚书学者并无区别。
南宋初《禹贡》新经解的主题,是强调皇权与国家统一的尊王思想,而朱熹对天下山川格局的重新整理、对冀州特别是河东地区的强调,都与《禹贡》的时代解释有关。朱熹眼中的天下山川是高度中心化的,但他所强调的并非具体的本朝王权,而是以尧、舜、禹为代表的抽象的华夏王权,寄托了儒家对文明延续的期待。这种以冀州王都为中心的地理新秩序,本质上是在风水学框架中糅合了多种世界观的理想主义政治地理学。
三、元代的堪舆地理学
朱熹彻底改变了堪舆术对天下山川形势的认识。在他之后,许多理学家持续向堪舆术士灌输这种“大风水”的理念,朱熹的天地风水论一步步下沉为社会的一般知识与信仰。
江西吉州人欧阳守道曾广览风水书籍数十种,认为其中有一种大约是“出于明理之儒者”,“最可人意”。这种优质风水书与普通风水书的区别在哪里?他说:“明理之书探山川融结之情,引经援史,远及四方郡邑之大势,可与识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只有从天下山川郡县之大势出发,才称得上是“明理之书”,而这样“引经援史”并且熟悉山川地理的著作,显然要求著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儒学及地理学修养。元代李祁对那些“拘其数而昧于理”的风水师不感兴趣,而一旦出现一位熟悉真实地理,畅论千里来龙,“山势之去留隐现,水势之向背趋舍”的,就立刻表示赞赏,还写序为之揄扬。以堪舆理论解释山川大势,事实上是儒家士大夫与堪舆术士之间的知识联结,此时正在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政治地理观念。
在这种新型政治地理学中,朱熹的天地风水论自然占据核心位置。在元代,有人见过一种“朱、蔡二先生《地理图》”,所描绘的就是昆仑为祖、“蟺蜿扶舆磅礴郁积之气聚于中州”的天地风水形势。理学家陈著晚年有一次接待风水师马元炎,他考校对方所学,马氏讲了一番“来冈去水,伏龙起峰”的道理,陈著不以为然,说:“天下有大阴阳、大器局,朱文公所谓在冀州之野,坐常山、太行之所盘结,左泰右华,以受嵩、衡诸山之朝揖,而长江、大河横贯于前,此则方为有所见而。既有志于此,不可以近且小者自画。”同一时代的风水师谭叔明得号“明山”,陈仁子就对他讲了一番“繇须弥出昆阗、涉太行,以太、华为对待,以衡、嵩为潮应”的大局势,还问他“亦尝明及此否”,所依据的也是朱熹的理论。郑思肖更把风水师须要了解的地理范围扩展到无远弗届的地步:“若不能见吾双足之下来龙,则不知吾眼底所见八方来龙;若不见吾眼底八方来龙,则不知此县此州、众山众水、一丘一壑各各来龙;若不见县州、山水、丘壑各各来龙,则不知九州、五岳、万山万水各各来龙,则不知至远八方、遐陬绝域、四大海中、一切大小山水、洲潭诸国、不与南阎浮提中国接壤之地各各来龙,毕竟毕竟不知渺渺茫茫、无边大地大海全体来龙。”儒家士大夫不断地向术数世界添加建构在宏观地理基础之上的世界观,希望风水师同时具备类似于今日所说地理学的素养,这种努力相当成功。元代有些风水师重视宏观地理,甚至到了吴澄所说“能原其来于百十里之外,而不能乘其止于一二尺之内,此察地理者之通病”的程度。
到宋末元初,朱熹的天地风水论开始进入堪舆典籍,成为术士修习的内容。题为北宋国师张子微的《玉髓真经》其实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篇幅铺陈这种堪舆政治地理学。在论述天下大势的部分,《玉髓真经》首列“唐虞冀都之图”,并将中国的核心部分比喻为人体:长安如首,洛邑如腹,冀都如左臂拳,建康如右臂拳。为何冀都在后世再也无法成为首都?那是因为“冀都下流之应”在碣石,汉代碣石沦于海,“冀之应已失矣,风水变迁,故不可都”。《玉髓真经》对冀都风水变迁的解释,实际上是利用堪舆观念来弥缝朱熹的冀州中心论,然而,这种说法虽然巧妙地因应了王朝政治变迁的挑战,却遗落了朱熹所坚守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传统。
普通的地理书、地理图,也开始反映出堪舆地理的影响。日用类书《事林广记》在元初刻了增订本,其中的《腹里图》看上去只是一幅普通的元代国都图,实际上却绘出了“皇都新城”的风水形势:元大都背后的居庸山被画成天下最高之山,居庸山伸出长城如双臂环绕国土,远处是祖山、蒙古山、木叶山隐隐来龙,皇都之前则是河水缠绕,东到碣石入海,南面北岳、太行、王屋、五台、东岳、芒砀等山皆作朝拱之势。特别是朱熹最为重视的太行,本来是绵延千里的巨大山脉,此处也与诸山一样,被画成一座孤峰,以免喧宾夺主。 另外一种日用类书《翰墨全书》的《腹里图》也大致相同。这与《玉髓真经》一样,都是看重“本朝”。虽然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在后世被不断重述,却极少有人主张建都于河东,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本朝”与“时王”的政治权威只可论证、不能挑战。
入元以后,关于中国山川大势的讨论仍在《禹贡》注解中继续,不过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已经少被提起。本来,蔡沈折中了一行和朱熹的理论,一方面否定三条四列的分法,将中国的山分成南北二条,即黄河以北与江汉以南两个部分;另一方面又说“河北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岚、宪诸州乘高而来”,重复朱熹的看法。然而,现存的元代《尚书》注解,如陈栎《书集传纂疏》,许谦《读书丛说》,黄镇成《尚书通考》,董鼎《书传辑录纂注》,王充耘《书义矜式》、《书义主意》、《读书管见》,王天与《尚书纂传》,朱祖义《尚书句解》等,都不再论及太行山的走向问题,其中陈栎、董鼎等书明确是为“羽翼蔡传”的,也对太行山的问题避而不谈。吴澄《书纂言》虽然也说太行是“天下之脊”,却因为“太行连亘河北诸州,泽州之晋城,潞州、怀州之河内、武陟、修武,以至于河北境,皆太行所经,故太行在河北为天下之脊”,完全消解了太行走向所蕴含的形势意味,太行也仅在河北区域之内为北条之“脊”而已。
但是,金履祥的《书经注》是个例外。从南宋末年到元代,该书在《尚书》注解中对山脉系统整理最为详尽。金履祥主张,王肃、郑玄只不过是将《禹贡》分章为条、分段为列,“若指为山势之脉络,恐未然也”,但是,“天地常形,固相为勾连”,山势的确有其脉络。他把中国山川分为源出昆仑的“三络”(只有泰山独立于三络之外),并以河流的不同流向判断山与山之间的脉络。他特别发明了“盘”这个概念,应对南方之山较为分散、不易连成脉络的困境,对南方之山的整理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详尽程度。金履祥所论及的地理范围已远远超出《禹贡》山川。与朱熹、蔡沈一样,金履祥也认为太行系代北、云中发脉而来,同时他也清晰地指出,代北、云中之脉源自昆仑。
明代风水师追溯三大干龙理论来源时,将金履祥放在龙脉论知识谱系中仅次于朱熹的位置。明代最著名的堪舆书,徐善继、徐善述兄弟所编《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简称《人子须知》)“总论中国之山”部分,先列朱熹关于山脉的看法,接着“复辑山水总说”,所引“仁山金氏”就是金履祥《书经注》的内容,在“山水总说”中占据了最大篇幅。
大体而言,将天下山脉三分的理论,是将江河两分法中的南方之山再两分,实质上是长江以南之山的“独立”。从自然地理上来看,北络、中络较易排布,但南方之山的堪舆布局一直是龙脉理论的难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之山确实不如北方有较为清晰的脉络走向;另一方面,南方也少有固定的全国性政治中心,朱熹也只能笼统名之曰“江南诸山”,或者分成几支,很难梳理出一条清晰连贯的山脉。经过蔡沈、金履祥等尚书学者的努力,南方之山的脉络才慢慢清晰。
与前述太行山相同,南方之山也存在一个走向的问题。较早的堪舆地理学附和山河两戒的说法,把南方之山描绘为北方山川的延伸。《撼龙经》云:“南龙高枝过总顶,黑顶二山雪峰盛。分出秦川及汉川,五岭分星入桂连。”“总顶”、“黑顶”等地名虽不易索解,但大意可知:南龙之山系随汉水而南,越过五岭,到达桂林、连州等地。但在经过朱熹龙脉论改造的山脉系统中,南方之山系由岷山生出,再向东、向北。南方之山之所以需要呈现出由南而北之势,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尧舜之都的案山,只有朝向北方,才能完成朱熹的大风水之局。
湖南、江浙之山多南北走向,但究竟是“南来”,还是“北来”,这不仅涉及堪舆形势的形成,也是气运转移、文教代兴的象征。韩愈曾说,衡山之南八九百里为郴州,“中州清淑之气”穷尽于此。元代程端礼对此非常不解:“天下山川,皆自西南入中州,后世地理家卜葬者所能知也,退之读《禹贡》,乃不知之,何邪?”所谓“天下山川,皆自西南入中州”,即指蔡沈所说的“岷山之脉,其北一支为衡山,而尽于洞庭之西”,岷山生出衡山,衡山向北尽于洞庭,这样湖南之山就是自南而北,而非如韩愈所说自中州而南了。
程端礼的话透露出,朱熹、蔡沈、金履祥式的山脉系统在当时已成为“地理家卜葬者”的基本常识。同南方山脉走向的重新定义一样,将天下山川分成三条脉络的观念很快为堪舆界所吸收,并被赋予政治功能。元末姚桐寿记载刘基语:“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北龙、中龙人皆知之,惟南龙一支从峨嵋并江而东,竟不知其结局处。”刘基认为,南龙结局在海盐诸山,“此南龙一最大地也”。姚桐寿问“此何人足以当之”,刘基说:“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无有乎尔,吾恐山川亦不忍自为寂寂若此也。”“结局”是风水概念,指的是龙脉之气所钟之地。刘基既然意在发现南龙之“结局”,则北龙、中龙之“结局”所在,应当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乐郊私语》作于元代末年(序于1363年),其时刘基尚未离世,姚桐寿系记其亲闻,而且是未能实现的预言,可信度极高。即便这段议论并非出于刘基,也可以证明在元代“善形家言”者之中已经流传三龙之说,而且到了“人皆知之”的地步。
无论是《玉髓真经》的国都风水变迁论,还是刘基的三龙说,较之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都有了根本性变化,那就是单一的冀州中心变为多中心,以适应对历代王朝国都的堪舆学解释。这些新理论可以很方便地为后世皇权提供堪舆论证,同时意味着堪舆地理学不再坚持朱熹天地风水论的政治超越性。恰好,在不久之后建立的明朝,都城与皇陵分布在范围广大的南北多处地点,三龙说与明代皇权迅速形成互证。
四、明代三都与三大干龙说的定型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死葬孝陵,令元代堪舆家感到纠结的“南龙结局之处”终于有了方便的答案。朱氏家族发源于凤阳,明祖陵、皇陵皆在濠、泗一带,明初又曾营建中都于凤阳,中龙结局亦不必再限于洛阳、开封。明成祖迁都北京,昌平天寿山成为明陵所在,在时人看来,这是中原王朝的首都自尧舜以后第一次重回冀州,更为北龙之王气提供了新的证据。于是三大干龙说迅速成为社会共识,既为堪舆家所津津乐道,也成为在一般士人阶层中流行最广泛的地理框架。
在民间,普通士人和风水师一直努力将三大干龙说与明代皇权联系在一起。王文禄记载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遇到徐献忠,后者说曾至凤阳,见“熙祖陵龙脉发自中条,王气攸萃”,并解释说,“元末东开会通河绕之,而圣祖生矣”。这又是一种动态的龙脉观,用以解释山川之灵何时而“发”的问题。徐献忠著有《大地图》,今虽不传,但从堪舆书中引述的片段来看,他确实是以大风水的视角来看待明祖陵的堪舆形势。
在庙堂,明代君臣自然也乐于接受这种理论安排。成化二十三年(1487),丘濬向新登基的孝宗进呈《大学衍义补》,其中“都邑之建”部分首先引述朱熹的天地风水论,幽燕作为冀州的一部分获得了作为首都的资格。在丘濬笔下,明朝都于北京不仅意味着得到了风水宝地的加持,而且延续了黄帝、尧、舜以来帝王之正统,明代皇权由此得到了地理与历史的双重证明。《大学衍义补》是帝王教材,在明清时期影响极大,朱熹的天地风水,乃至以堪舆观念理解天下大势的方式,至此正式进入帝王的视野。只不过,《大学衍义补》虽然名为补充朱熹弟子真德秀之《大学衍义》,其建都论却与朱熹有着巨大的差异:朱熹的天地风水论是一种理想主义设计,是不满于偏安的结果;丘濬的说法是对王朝既定政治现实的肯定与解说。
现有的堪舆类文献中,对三大干龙说表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是前引徐善继、徐善述的《人子须知》。徐氏兄弟是江西德兴人,青年时遭家难丧父,他们不忍以大事付“俗师”,于是弃去功名,究心堪舆,遍历名山大川,终成一代堪舆名家。徐氏兄弟以30年之功著《人子须知》,该书在隆庆二年(1568)前后第一次刊刻,迅即流行开来,成为知名度最高的堪舆典籍之一。《人子须知》以总论天下大风水起首,然后分论三大干龙:南条干龙指“大江以南”之山,其脉起自岷山,经云南,东趋夜郎,逾桂岭为九嶷山,又入岭南,再过大庾岭进入江西,抵信州、徽州,东行为天目山,然后分为四支,一支赴杭州,一支入海门,一支为南京,一支逆江而上至鄱阳湖;中条干龙指“大河以南、大江以北”之山,其脉起自西倾,经陇右,过凤翔,向东入河南后分出三支,一支出熊耳,为嵩山,“其后脉乱于河”,再出兖州,为泰山,一支尽于登州、莱州,一支尽于沧州、棣州;“中条干龙又一支”自嶓冢西行湄州、汉水之间,出武关,抵信阳,行淮水之南,尽于南通州;北条干龙指“大河以北”之山,其脉起自昆仑,至白登,西一支为壶口、太岳,次一支南出为析城,又西折为雷首,又次一支为太行,再次一支为燕山,尽于平滦碣石山。《人子须知》最后说,以上“中国诸山皆始昆仑,分派四列,以遍九州”。
徐氏兄弟本是儒生,而且世传尚书学,这套理论与《禹贡》经解传统有密切关系。他们的三龙说脱胎于金履祥的三络,最明显的证据是其“中条干龙又一支”与金履祥的“中络之次”完全相同。但是,《人子须知》并不只是如金履祥一般在整理山川,在这种堪舆地理学中,南龙结为南京及孝陵,中龙结为明祖陵及“大礼议”中新追尊的显陵,北龙结为北京及天寿山皇陵,原有的天下山川、五岳等,都让位于皇都与皇陵,皇权彻底垄断了天下的风水景观,所谓“三干之尽,惟我朝独会其全”。同时,《人子须知》还历数历代国都,称北龙首结北京,次结平阳、蒲坂;中龙首结丰京、镐京、咸阳、长安,次结洛阳,再次结汴梁;南龙首结南京,次结临安。历代国都也在这样的堪舆地理中获得了解释。自然,在历代国都中,《人子须知》极力渲染北京的优越性。曾任刑部主事的唐枢认为北京仅是“枝结”,而非“正结”,《人子须知》直斥其为“妄谈”,借用丘濬而将朱熹所说的“冀都”硬指为北京。北京处于北龙之上,《人子须知》就将北龙描述为“昆仑之中脉”,因为“以华夷共视为中脉,盖鸭绿江外又有大干为护”,北京在风水格局中也获得了华夷共主的地位。
从风水角度对本朝皇权正当性的论证,不但在堪舆类典籍中处处可见,朝堂上也常常谈及。如嘉靖年间曾出任南京兵部尚书的韩邦奇所谓“江淮之间,风水最大”,只不过是闲议论;但在遇到家国大计之时,龙脉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坚实的论据。万历二十七年(1599),叶向高在反对开矿征税的奏疏中,以开矿破坏孝陵龙脉为由,三龙说已被他运用得相当娴熟自然。潘季驯治理黄河,也不得不引用《地理心学》等堪舆书,反复强调“祖陵风水来自中条”之类,不但为自己的治河之策张本,而且还作为应对各路阻力的武器。崇祯十四年(1641),礼部侍郎蒋德璟奉命勘察皇陵之后,奏称“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结为凤、泗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诸陵。这三大干本朝独会其全,真是帝王万世灵长之福”。崇祯皇帝回称:“这三大干都从昆仑山发脉来。”君臣对话与《人子须知》所述若合符契,三龙说已经成为社会的共享知识。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热衷于游观山水的士人,他们虽不从事堪舆职业,但会用堪舆的视角去观察天下山川,特别是宏观的山水地理形势。明代最著名的两位旅行家王士性、徐霞客都是如此。
王士性《广游志》卷上“地脉”条所论“三龙”已被学者广为讨论,此处不再赘引。《广游志》是王士性对于一生游踪的理论性总结,“地脉”是《广游志》的第一条,开头就说“自昔堪舆家皆云,天下山川起昆仑,分三龙入中国”,正是以堪舆家的三龙说来理解中国的基本山川。但是,王士性“九州历其八”,亲身到过川、滇、粤,他以得自目验的地理知识改进、发展了堪舆家的三龙说。例如前引《金壁玄文》及《人子须知》都说南龙与中龙同出于岷山,这种说法源自朱熹、蔡沈,王士性就批评说,金沙江已经切断岷山,所以岷山只出中龙,南龙系由吐蕃之西而来,经云南、贵州到湖南,再分为五支,布满长江以南。
相较于《人子须知》将三龙与明代皇权地理互相匹配的做法,王士性一方面重复明朝“兼三大龙而有之,安得不万斯年也”的旧论,另一方面构造出一套气运转移的历史哲学。他的三龙论本来就是为了回答经济文化重心向南转移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般都以“天运循环,地脉移动”来解释,但是不得其详。王士性则以“王气”在三龙中“发”的先后来回答:“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北龙次之,南龙向未发,自宋南渡始发,而久者宜其少间歇,其新发者其当坌涌何疑。”“发”也是堪舆术的概念,指的是吉地的“应验”。在这个理论中,“声名文物”的消长首先被归结为“王气”的转移,“王气”成为融合政治中心与社会繁荣于一体的概念。同时“王气”也是历史性的,各龙都是先发其末,再循而上之,那么“今南龙先吴、楚、闽、越,安得他日不转为百粤、鬼方也?”
在王士性的影响下,徐霞客在旅途中也特别重视南龙之山,《徐霞客游记》中有多处将某处山脉指实为“南龙正脉”。他的《溯江纪源》沿袭王士性对宋儒以岷山为南龙之起的批评,同样强调南龙之重要,“今详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而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南龙之长,还有长江作证明,“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此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南方之山,在朱熹那里只不过是冀州王都的重重案山,经过元明禹贡学者与堪舆家的整理,不但南方的山川脉络越来越清晰翔实,而且地位也越来越独立和重要,在王士性、徐霞客的笔下甚至超越了北方山川。
王士性、徐霞客的三龙说来自堪舆地理又加以修正、发展,在他们看来这套理论是实存的、可以验证的地理形势,“本朝”与三大干龙的配合关系也被他们一再提起。不过王士性的著作流传很少,《徐霞客游记》到清代方才刊刻,明代流传的三龙说仍然是《人子须知》式的,像《雪心赋直解》《地理琢玉斧峦头歌括》等堪舆类典籍莫不如是。即便是重视星气的堪舆类书籍,也往往会先设定一个以昆仑山为中心的世界观,只不过这派堪舆术中的龙脉更具术数色彩而已。
堪舆世界观与宏观地理学,三龙说的这两种色彩在晚明以后并行不悖。即以类书为例,前者如刊于万历三十七年的《三才图会》,该书地理部在龙、砂、水、穴诸图之后的最后一图即《中国三大干图》,并抄录了《人子须知》“总论中国之山”、“总论中国之山水”两条内容,仍将三龙说当成一种堪舆理论。后者如章潢《图书编》地部首卷为分野,次卷先列“天下山川海岳大势图”标题,所绘图像却是《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文字部分则与《人子须知》总论天下山川部分大同小异,这样的排布就不再把三龙说视作堪舆术,而是宏观地理学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全文收录了王士性《五岳游草·地脉》,这意味着全国性政治地理专著也开始采纳三大干龙的理论。
结 论
作为宏观地理学的一般框架,龙脉论影响中国地理学长达数百年。1925年,地质学家翁文灏有感于“明清言山者之旧说”与“英美日本所出简单而非科学的图说”主导中国地理教科书图本的现状,撰成《中国山脉考》,这是第一篇以现代地质学与地理学的观念重新全面审视中国山川的学术论文。翁文灏所谓“明清言山者之旧说”,指的就是形形色色的龙脉论。但是,学术的演进不能代表普遍观念的更新,龙脉论仍然流行于一般社会,如到了1934年,丁文江还在《再版中国分省新图序》里面奉劝同行“少讲些龙脉”,这样才能让“中国青年渐渐的了解地形是怎样一回事”;1936年,王庸还在愤恨于“玄学式的山脉观念和堪舆家龙脉之谈,却依旧流传于现代的中国”。
本文的梳理证明,这套理论既不是堪舆家的独家专利,也不是若干儒家学者如王士性等人的独立发明,它存在一个复杂多线的演变过程,是多个知识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来自河洛纬书的神话地理学、《禹贡》注疏的经学传统、理学家的大地空间观念、对真实地理的认识与测量,都是龙脉理论的思想资源,但是促使古人将许多独立的山脉连成特定脉络的真正因素,却是知识背后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朱熹的天地风水系统,背后是南宋前期尊王的政治呼吁、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以及对北方故土与华夏正统的坚守;明代堪舆家的三大干龙说,背后则是南方地位的上升,以及对本朝皇权的呼应。
真实世界中的山脉万古不移。然而,如何整理、理解山川形势,如何赋予其或边界、或脉络、或神圣的意义,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主观建构。这套关于中国龙脉的理论既有自然地理的根据,常以讨论自然地理的面貌出现,又有等级性的文化地理成分,但最终是一种政治地理。唐晓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之学主要是王朝地理学,“它的核心是讲述、解释、捍卫王朝的社会空间秩序”,经过王朝地理学的讲述,自然的山川大地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王朝的“江山”,龙脉论所描述的中国干龙系统自然也属于这种王朝地理学的一部分。不过,堪舆意义上的龙脉论重点在山川脉络的“结局”或“吉地”,社会心态所关心的也往往是建都、皇陵、“王气”,乃至潜在的未来皇帝,这样的龙脉论其实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它一方面表现为堪舆世界观,是堪舆术中较为重视宏观山川地理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地理学中经常被附会以堪舆色彩的部分,或许可以称作“皇权地理学”。
不过,除了为皇权提供论证的一面,龙脉论也是流传于社会一般心理之中的国土观念。堪舆家通过一套拟象化的宗法观念,以龙脉/山川为管道,经过干龙—郡县来龙—祖山等层次,把个人与“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似乎每个个体通过这套堪舆世界观而与天下相联系。同时,由龙脉所定义的中国也会随着国土的扩展而延伸。核心区域稳定、边界伸缩不定的中国,存在于作为一般知识与信仰的龙脉论之中,特定的地理区域与中国文明也因此具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然而到了清代,来自北龙以外的人群统治了中国,新的政治格局与三大干龙理论产生了尖锐冲突。龙脉论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之大,以至于对统治基础怀着强烈焦虑的康熙皇帝感到有必要予以认真回应——他挟西洋新术,以帝王之尊亲自改写了清王朝的地理脉络,而朝野上下则另有一番应对。篇幅所限,那是另一篇论文的主题了。
作者段志强,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1、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2、本网诊治疾病的文章仅供参考,不能据此自行确诊和进行医疗;
3、本网转载文章为传播更多知识,在未声明禁止转载的情况下予以转载。图文视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发邮件至 shushanpai@guozhi.org.cn 联系删除。

